
《狂野時代》: 影像考古與美學再生的實驗
《狂野時代》是齣容易令影迷長篇大論的作品,借鑒或聯想到的經典名片不勝枚舉。乍看之下,導演畢贛如同塔倫天奴(Quentin Tarantino),「影癡」上身,將熱門、冷門、邪門的電影,收入囊中,化為新作橋段。且看《危險人物》(Pulp Fiction) 的招牌舞姿,脫胎自費里尼(Fellini)的《八部半》(8½)。
但實際上,畢贛打從《路邊野餐》的意識流鏡頭開始,彷彿替塔可夫斯基(Tarkovskiy)借屍還魂。期間敘事迷離、詩意旁白、長鏡頭跟拍,在畢贛電影中和睦交織。這些藝術片手法,可謂似曾相識,卻自成一派。尤其《路邊野餐》的私人抒情,風格貫徹。然而《地球最後的夜晚》借鏡塔可夫斯基的意象,又是《潛行者》(Stalker)那樣,水杯在桌上顫抖,又好比《鏡子》(Mirror)天旋地轉,畢贛才有了拼湊之嫌。

塔可夫斯基作為蘇聯時期的電影天才,以歷練翻新藝術電影的跨類型表達。(《潛行者》劇照)
塔倫天奴好歹是合併成新章,到《狂野時代》,畢贛乾脆把百年影史復活,致敬的電影比塔倫天奴更主流、更有而為之。唯獨沒有鬼才口吻,偏向莊重的指涉。《狂野時代》中,畢贛先假設,全人類停止做夢,只有易烊千璽飾演的 「迷魂者」可以搖身一邊,附身到五段生命。
「迷魂者」是電影本體幻化成人,據畢贛所述, 最初就叫「電影怪物」,難怪造型來自茂瑙(F. W. Murnau)的《吸血殭屍》(Nosferatu)。所謂五段生命,代表五感,也反映五類電影。以畢贛影射佛學的舊例,《狂野時代》的概念對應佛教「六根」。好讓「迷魂者」生死輪迴,在電影語言的渲染下,和觀眾心靈相通。就這樣,《狂野時代》為求沉浸,可以無所不為,調度和美學愈多愈好。說是看罷經歷了好幾齣戲也不為過,貪心又別有玄機。
開篇由視覺主導,「迷魂者」誕生是默片格式,久違的間幕、復古畫幅和悠長配樂,代替了現場音效,呈現深諳電影術的「大她者 」(舒淇 飾)在封建社會,解放困於鴉片館的 「迷魂者」。形式和內容上,瘋狂致敬最早一批挖掘電影的先驅。包括「大她者 」 走過微縮場景,根本是佐治梅里愛(George Méliès )的技法,復刻了《月球之旅》(A Trip to the Moon)。

「大她者」讓電影起死回生,建立異度空間。(《狂野時代》劇照)
轉眼到壓抑而超現實的佈景,召回德國形式主義的風采,和舊時代的扭曲和混沌,氣氛契合。兩人還重演有「世上第一齣喜劇」之稱的《水澆園丁》(The Sprinkler Sprinkled), 更為了扣題「視覺」無所不用其極,前後演繹《科學怪人》(Frankenstein)與《聖女貞德》(The Passion of Joan of Arc)那重見天日後動容的眼神,令人肅然起敬,不敢有微言。正所謂「傑出的創作人模仿,偉大的創作人剽竊」,《狂野時代》飲水思源,以歌頌電影的名義,肆無忌憚地「剽竊」,不失是富有尊嚴的算計。
當《狂野時代》的格局已定,接下來的篇章便各司其事。第二章告別了無聲電影,轉為聽覺操縱。「迷魂者」和某音樂家在鐵軌撕扯,鬧出命案,惹來陰險毒辣的警探(趙又廷 飾)深究。「迷魂者」稱自己體內的天籟之音,過分動聽,是禍亂根源。如此魅惑,宛若蛇蠍美人的定位。最終警探為求真相,更不惜撕破耳膜。如此極端的自毀,伴著煙霧迷漫、陰影濃烈的畫面,絕對是黑色電影再現。期間合眾爭奪的神秘音樂盒,是推進劇情的核心,形成勢派交鋒。此處的技法,搭以變焦鏡頭,都出自懸念大師希治閣(Hitchcock)。當畢贛遇上希治閣,擾人心魂之餘,亦玩弄懸念。

「迷魂者」首先遊蕩於一片朦朧的犯罪之都,純然的諜戰片格調,怪誕又猛力。(電影劇照)
尾段的鏡房槍戰,除了帶有傳統的鏡子意象,反映人格上的一體兩面,更顯然搬演奧遜威爾斯(Orson Welles)的名作《上海小姐》(The Lady from Shanghai)。但這並非畢贛獨創,譬如香港觀眾熟知的杜琪峰,已在《暗花》、《神探》的重頭戲仿效,活地亞倫(Woody Allen)的《曼克頓神秘謀殺案》(Manhattan Murder Mystery)也曾套用,堪稱潮流。整體看來,此段的情調和調度順暢,不過「聽覺」的命題,雖然在文本和意念上屢次強調,但音效設計是否最突出、最前瞻,足以獨領風騷?似乎未至於。
(未完待續)
狂野時代
上映日期:2025 年 11 月 27 日
 Add a comment ...
Add a comment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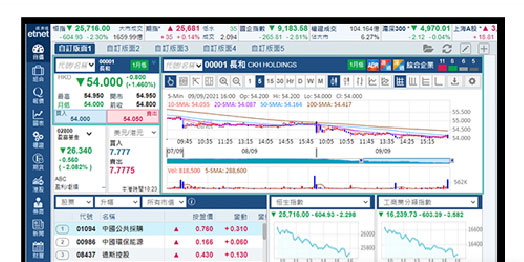














Comment
暫無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