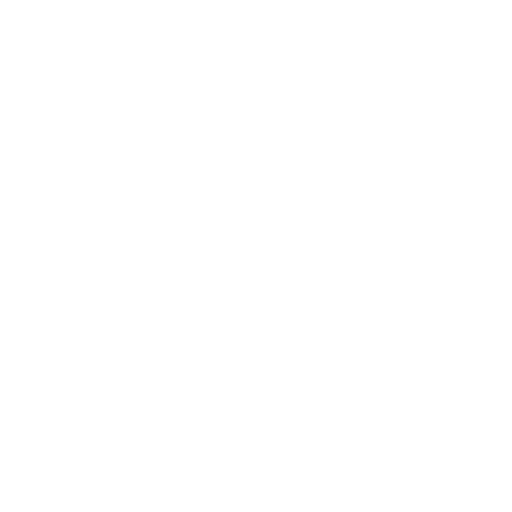29/08/2014
入得秘魯廚房
TJ 及 KJ
TJ 及 KJ
Long Way Home是一個旅程,兩個80後香港平凡男生添仔 (TJ) 及甘仔 (KJ)在不乘搭飛機的情況下,從南美洲的智利,以陸路及水路回到亞洲香港的家。途經4大洲、33個國家,順序為智利、阿根廷、玻利維亞、秘魯、厄瓜多爾、哥倫比亞、巴拿馬、哥斯達黎加、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危地馬拉、墨西哥、美國、英國、法國、西班牙、意大利、梵蒂岡、聖馬力諾、克羅地亞、波斯尼亞、塞爾維亞、科索沃、黑山、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土耳其、羅馬尼亞、摩爾多厄、烏克蘭、俄羅斯、蒙古、中國,最後經羅湖回港,需時約9個月至1年。
Long Way Home
逢周五更新

利馬市內有超過6000間不同規模的中國餐廳,感覺比得上麥當勞在香港的密度。當地人叫中國餐廳做 CHIFA,等於普通話的「吃飯」,普及程度連鄰國玻利維亞及厄瓜多爾也開始有CHIFA。距離中國那麼遠的南美國度,竟然有如此多熟悉的食物,引起我們的好奇心,於是試試跟這些CHIFA的負責人作些訪問。
在秘魯的CHIFA,大多數是廣東人開的,有小部份屬福建人的,所以訪問可以盡情用廣東話來進行。其中來自廣東開平的英姐,在秘魯已經20多年,最初因姑媽說這裏有很多商機而來,一留便落地生根,她的兒子在秘魯出生,有著廣東人的面孔,西班牙語卻比廣東話流利。

CHIFA賣的食物大同小異,種類很多,通常以炒飯炒麵配其他食材,例如甜酸雞肉,雲吞湯麵也有。最受秘魯人歡迎的是炒飯,據觀察所得,南美洲很多地方也有CHAUFA這道菜,也就是炒飯的譯音。英姐跟我們說,正宗中國菜當然不只是炒飯那麼簡單,但本地秘魯人就是喜歡吃,而且他們愛吃豉油,很多食物都偏向重口味,所以 CHIFA跟我們廣東人吃的當然有出入。


我們在秘魯唯一的Couchsurf主人Karin,在利馬一間銀行工作。今年39歲的她屬主管級,有車有樓有品味生活無憂,她的家在利馬的低密度住宅區La Molina,感覺像香港的九龍塘。跟姐姐同住的她,邀請我們周末跟她家人共進午膳。

我們打算為Karin一家預備午餐,希望弄最擅長又有信心的卡邦拿意粉,不知道為甚麼突然變了弄中國式炒飯。不擅拒絕的我們,只好接受挑戰。未曾弄過炒飯宴客,一來便要為6位秘魯女士弄午餐,心情非常緊張。Karin特別跟家人提起我們,她的媽媽及祖母更在午餐當天親自在廚房看著我們弄菜,謙虛地說想向我們學習做中國菜。幸好在高壓情況下我們成功做了入得口的炒飯,Karin一家人更把整碟吃光,總算放下心頭大石。



來到秘魯利馬,代表攝影師Jovi將要回港,結束他短短的3星期旅程。經過智利、玻利維亞及秘魯的陸路旅行,起初害怕他受不了我們食得平、住得差以及為節省旅費經常步行的宗旨,現在Jovi已經蛻變成一個捱得之人,即使鞋底破爛也毫無意見地跟我們穿州過省,坐24小時巴士也不買飲品堅持3人共飲一支水。2015年初,Jovi很有機會在歐洲或中東地區重返團隊,繼續他未完成的錄影。我們隨時歡迎他加入,因為這3個多星期的旅行很開心。
離開利馬後我們取道北部小城Chiclayo,準備離開秘魯到另一國家厄瓜多爾。
TJ
今年5月底離港前跟大學朋友道別的晚餐裏,Jovi才知道Long Way Home這件事。席間他提議過在旅程開始後飛到智利會合我們 ,短暫跟我們旅行一小段,途中會拍攝當中點滴,之後回港再剪輯成短片作為記錄。想不到一個小小的討論最終成真,來到Jovi離開Long Way Home的那天,失落感很重。3星期的旅行令我們3個麻甩仔更緊密,Jovi離開後的幾天, 完全沒有拍照的慾望,且時常看到他的影子。在旅館的天台,看見一條紫色大毛巾掛在外面,我們立即拍了照,發了Whatsapp短訊給Jovi ,因為它的顏色跟Jovi離開秘魯前丟棄的那條一樣;在餐廳看見有人吃剩食物時,KJ自言自語地責怪Jovi,因為Jovi的胃口細,經常不能清光食物,看不過眼的KJ會向他訓示一輪,然後把吃剩的掃光。
跟利馬的Couchsurf主人Karin了解過當地的CHIFA境況後,心裏有一點為廣東菜平反的念頭,在秘魯人心目中的中國菜只有炒飯炒麵?!加上那次午餐炒飯挑戰成功過關,我們自薦為Karin弄晚餐,好讓她放工回來可以試試兩道小菜加白飯任裝。記得媽媽說過,煮菜要用薑加蒜,醃肉用豉油鹽糖生粉。我們到街市看過, 決定弄兩道港式家常小菜:脆肉瓜牛肉及番茄炒蛋。兩道菜非常似樣,跟 KJ 試味後,吃出媽媽的味道,但不肯定合不合吃慣 CHIFA的Karin的口味。起初她不斷大讚好味,最初不肯定是客套話還是甚麼,最終她添了3次飯!這次的大成功,令我們信心大增,在往後的 Couchsurf裏,可以兩味菜走天涯。另外有一有趣題外話,在秘魯本地人口中,薑跟豉油的讀音跟我們的廣東話一樣,明顯是因為CHIFA的影響。

多年來一直逃避重看《鐵達尼號》,因為很害怕看到即將沉船的那幾場戲。小提琴手們在甲板上完成演奏後開始解散,其中一位琴手突然有感而發,獨自「安歌」再次奏起音樂。他的行徑引起其他琴手的注意,在混亂的逃走人群裏,紛紛回歸樂隊再次一起表演。在小提琴的哀歌伴隨下,另一方面,鏡頭追蹤著幾個等待死亡的場面:無奈的船長在駕駛室看著逃難的乘客;白髮老夫妻在漸漸入水的房間裏互相緊抱在床上;小朋友在床上專心聽著媽媽講故事,同樣地房間裏也漸漸入滿海水。這首哀樂,這些畫面,多年來一直在我腦海重複,久未能平復。 從秘魯 Cuzco 往首都利馬途中(又一次20多小時的巴士路程),巴士小姐在當晚選了這部非常適合 time killing的電影, 我考慮過乾脆播歌睡覺避開它,但一直不能入睡。既然來到這一步,不如面對它,那怕 KJ 及 Jovi 見到我以淚洗面(這就是避看《鐵達尼號》的原因)。 我一直想不通,若果身處當時的鐵達尼號,我會選擇跟白髮老夫妻一樣放棄求生,抑或跟 Jack 及 Rose一樣堅持生存到最後一刻。2014年8月的這程秘魯巴士中,我依然未能選定。

KJ
我們在利馬除了想了解一下CHIFA 這個中秘合璧的產物外,並沒有甚麼特別的東西想做或景點想去。這天我們到了市中心都只不過是為了購買往下一站 Chiclayo 的巴士票,但反正出來了,那就即管行個圈吧,看一看首都的市況,說不定會有驚喜。
一如所料,市裏的情況沒甚麼特別,就像白天灣仔的莊士敦道,有各式各樣的小商店和多不勝數的 CHIFA,城市人在一片叫賣聲和汽車響按聲下,在熙來攘往的街道上與我們擦身而過。當然我們也有經過很多古舊有特色的建築和廣場,可是我跟 TJ仿佛對這些東西都感到麻木,連停下來拿相機拍個照的意欲都沒有。渾渾噩噩的亂走之際,TJ看到遠處的國家體育館,我們不是秘魯國家隊的粉絲,認識的球員來來去去都是那幾個,但身為足球迷的我們難得來到,也想去朝個聖,二話不說飛奔過去,可惜最後事與願違,大閘鎖上了,我們被拒諸門外。

失望兼疲累,我們決定回家,可是又不知道在哪裏乘車,到處問人,每個都給我們不同的答案,有的說車站很遠,有的又說隔幾個街口就有,被搞得糊塗的我們,花了一個小時連上車的位置到找不到。突然迎面走來一群小女生,向我們報以親切的笑容,機會主義者TJ 抱著博一博的心態向她們問路,怎料她們真的幫到忙,告訴我們要先搭車到一個地方再轉車,之後更帶我們到車站陪我們等車,其間不停發問,哪裏來幾多歲為甚麼來利馬(下刪一百條),感恩的我們當然逐一回答。臨上車前她們說叫跟我們做臉書朋友,在沒有廢紙的情況下,我們把名字寫在其中一個女生的手腕上,最後我們也順利回到 Couchsurf 主人家裏。

回到家裏一登入臉書,便立即收到小女生們的訊息,然後整個晚上的時間都奉獻了給她們。其中一個問起我們第二天甚麼時候離開利馬,說要跟我們作最後道別,我們半信半疑,但都告訴她巴士公司名字和開車時間。翌日來到車站,三個女生真的來了,已在那裏等待著,受寵若驚的我們趕快把行李寄存好,把握最後時間在登車閘口前和她們聊了一陣子,原來她們正在讀旅遊業管理,所以對外國遊客很感興趣,不過根據她們幾個女生的臉書,我們更相信實情是她們當初以為我們是韓國人(KPOP在秘魯紅得不得了)。
一個美麗的誤會,造就了這段八十後跟九十後的跨國友誼。

《經濟通》所刊的署名及/或不署名文章,相關內容屬作者個人意見,並不代表《經濟通》立場,《經濟通》所扮演的角色是提供一個自由言論平台。
【你點睇】港鐵失倫敦伊利沙伯線專營權,你認為「國際化」遇挫的港鐵應否將重心轉移回本地?► 立即投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