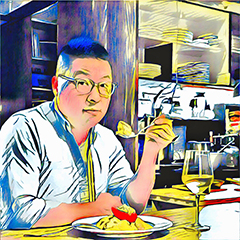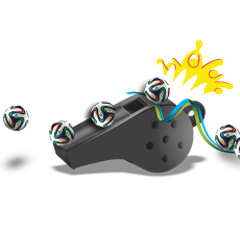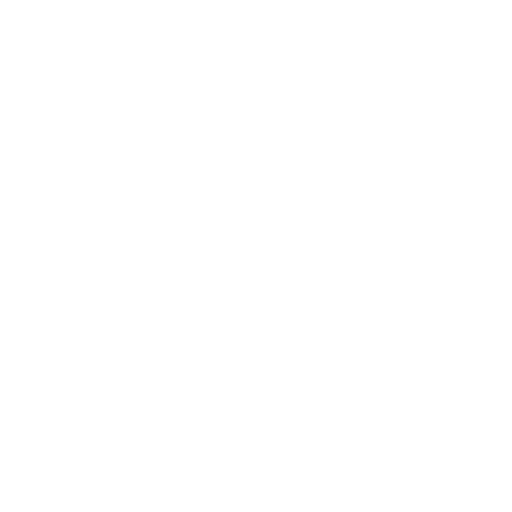28/04/2022
弱國有外交?芬蘭化模式的兩面性
俄烏戰爭的起源,坊間已經有了非常多的分析,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烏克蘭無視俄羅斯的安全需求,在西方欲拒還迎的誘惑之下,執意要求加入北大西洋公約(NATO)這個美國主導的軍事同盟,最終引來了俄國的軍事打擊。這似乎是一個小國外交失敗的典型案例(儘管戰爭終局尚未出現),不少論者提出了一個小國外交成功的重要案例:芬蘭化模式,認為烏克蘭其實本應走向芬蘭化模式,才能既保護自己國家獨立地位,又不至於惹毛了俄羅斯。故此進一步認為,未來烏克蘭還是應該學習芬蘭,才是保存自己的最佳道路。
這種觀點不能說完全錯誤,但至少不是完全正確。嚴格來講,是說對了一半,卻又遺漏了另一半。
不激怒強大鄰國,保存地位
先說說對的那一半。所謂芬蘭化模式,是芬蘭對瑞典和蘇聯這些龐大鄰國所採取的一種外交政策原則。簡單來講,就是盡量不激怒遠比自己強大的鄰國,以換取鄰國容許自己保持獨立的國家地位,至少保持高度自治的政治地位。這聽起來有點苟且偷生的意味,的確是如此,因此很長時間以來,芬蘭化或者芬蘭化模式,在西方國際關係學上是一個略帶貶義的術語。這個術語的提出,是在60年代冷戰時期的西德。當時西德總理的外交政策方針是儘量與共產國家東德進行友好緩和的交往,這引起了保守派政黨的群起攻擊,稱總理的外交為「芬蘭化」,旨在批評其怕得罪共產國家陣營,所以放軟姿態,屈從蘇聯東歐陣營。
(Shutterstock圖片)
西德保守派政黨之所以把自己總理的外交揶揄為「芬蘭化」,是因為當時芬蘭採取的討好或者不得罪蘇聯的外交政策,包括:二戰結束之後,不加入美國的馬歇爾重建計畫,反過來適度加大與蘇聯的貿易聯繫;更不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這個西歐反蘇軍事同盟,避免刺激蘇聯的軍事報復;冒著被指控為打壓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風險,立法限制芬蘭國內的反蘇聯聲音,甚至禁止或者銷毀某些反蘇聯的出版物等等。如此自我約束,換來了蘇聯包括斯大林在內的領導人的容忍,既沒有對芬蘭採取軍事入侵行動,也沒有支持芬蘭境內歷史悠久的左翼政治勢力奪權,成功地保護了國家的獨立性和民主政體的完整性。值得留意的是,在1940年蘇聯-芬蘭戰爭中,本來芬蘭國內的政治內訌極為嚴重,在意識形態上高度認同蘇聯共產主義的左翼政黨,居然在戰爭爆發之後,迅速與右翼政黨達成和解,停止政爭,一致槍口對外,保家衛國,抵抗蘇聯入侵。因此,在二戰結束之後,蘇聯其實對芬蘭的左翼政黨並沒有多大的影響力。
一言蔽之,這是用退讓妥協和自我抑制來換取強大鄰國的容忍,這是眾所周知的「芬蘭化模式」。
但如果我們從更長遠的芬蘭建國歷史來看,就會發現,其實芬蘭外交並不只是退讓妥協。16-17世紀(相當於中國明朝後期、清朝初期),芬蘭屬於當時的軍事強國:瑞典王國。芬蘭境內的「原住民」不僅尚未形成成熟的「我是芬蘭人」的獨立民族身分認同,而且整個社會上層都是廣泛採用瑞典語作為溝通語言。但當沙皇俄國在大北方戰爭中,沈重打擊和削弱瑞典王國之際,芬蘭人的民族獨立身分意識萌芽和迅速發展,趁著瑞典被擊敗的機會,開始了去瑞典化、強芬蘭化的社會文化變遷。儘管芬蘭並沒有因此而得到獨立國家的地位,但在沙俄從瑞典手中割佔芬蘭之後,沙俄給予了芬蘭當地人比較大的自治權,而不是採取中央集權式的管治。換句話說,芬蘭雖然沒有獨立,但卻充分利用沙俄和瑞典之間的戰爭矛盾,擺脫瑞典,發展自身民族認同,獲得自治的政治權利,從而拉開了民族國家建構的歷史進程。
捕捉機會,爭取政治權利
到了19世紀後期,沙俄忽然大大加重了對芬蘭的直接管治,許多原有的自治權力被逐漸取消,沙俄的芬蘭總督、負責對芬蘭進行文化蠶食的官員、駐軍、軍警和特務人員,越發加緊對芬蘭的管治力度,最終要達到同化芬蘭社會、完成俄羅斯化的政治效果。芬蘭社會當然無力對抗強大的沙皇俄國,但到了20世紀初,經歷日俄戰爭和一次大戰接二連三的戰敗,沙皇俄國在芬蘭的管治開始鬆動,芬蘭社會各派政治勢力敏銳地捕捉到了機會,利用沙俄勢力衰退、蘇維埃政權尚未站穩腳跟的大好時機,迅速爭取到了國家獨立地位,即使獨立之後陷入了內戰,也沒有失去獨立而重現被外國佔領。
整個芬蘭的國家獨立史,簡直如同毛澤東的十六字游擊戰真言那樣: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這才是完全的芬蘭外交模式。如果從這個歷史角度來看待今天芬蘭準備申請加入北約,共抗俄國,那麼就很容易理解了!
《經濟通》所刊的署名及/或不署名文章,相關內容屬作者個人意見,並不代表《經濟通》立場,《經濟通》所扮演的角色是提供一個自由言論平台。
【你點睇?】特朗普當局擬關閉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你認為若其關閉是否可促進全球和平穩定?► 立即投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