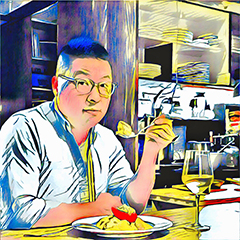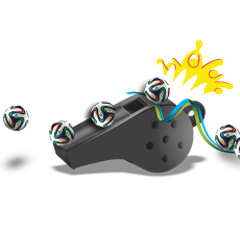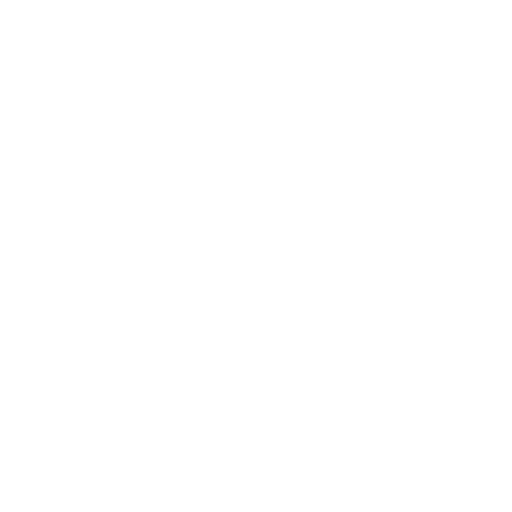29/04/2010
對自由的迷茫
談自由是個大題目,古代中國的自由觀是不問世事,優哉悠哉,像古老歌謠帝堯時代的《擊壤歌》所描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自己耕田、自己吃飯,帝王要幹任何事,於我何幹?只是這種自由是有條件的,要天下太平,帝王無為而治才可以。否則帝王橫徵暴斂,弄到民不聊生,講與世無爭只是唱高調罷了。
中國人講自由令人想起莊子。但莊子的字眼是「逍遙」,不是自由。逍遙的前提是無待,毫無制約條件,只是在現實世界根本不可行,連老子道行高超,也要感喟「人之大患,在吾有身;若吾無身,吾有何患?」人的身體是副臭皮囊,有很多需求,吃飯拉屎睡覺,因此一般人講逍遙談何容易,那是精神解放,只能說是一種嚮往的境界,或是美學的鑒賞,可以講藝術而不可以論政治。
與西方不同,中文的「自由」缺乏政治內涵,只不過是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的心境。 有政治涵義的自由是舶來品,那是來自十八世紀的法國大革命,高舉「自由、平等、博愛」的旗幟。
西方談自由,英文的freedom 和liberty,兩者都反對外界強加諸己的制約,但前者較重「個體自由」,後者則提升到涉及國家和民族的「集體自由」,並且特別強調自由選擇的權利。
有政治涵義的自由,在五四運動期間傳入中國,一時之間,愛自由之風有如「人來風」,一些自由金句,例如「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或是「不自由,毋寧死」之類,高唱入雲,但究其實,也不過是「風弄竹聲,只道金佩響;月移花影,疑是玉人來。」真正的自由沒有來臨,因為無論是香港人或是內地同胞,始終不知自由為何物;不知怎麼做才能自由;更不知得到自由以後接下去想幹什麼,所呈現的是對自由的一片迷茫。
對自由的最大誤解是以為自由容許放任,可以胡作妄為。其實西方人論自由也無絕對的自由,只有相對的自由,自由是立足於不損害他人自由的基礎上。西方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大師穆勒(J.S.Mill)在其《論自由》(嚴複譯為《群己權界論》)一書,言明自由應受限制,不容許有危害社會的自由。
二十世紀的自由主義理論家柏林(I. Berlin)更有「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之分。「消極自由」指出人的行為與公共社會的自由成反比,個人自由愈大,公共社會的自由愈少,因此私人空間與公共權威之間,要劃清界線,而界線劃在何處,是爭論所在。至於「積極自由」,是個人自由與外力制約成正比,兩者的爭拗愈多,民主反而卻步不前。
無論如何,如今所謂「自由」而成為一個神聖不可侵犯的字眼,但我想起法國大革命時被雅各賓党人送上斷頭台臨刑前羅蘭夫人的一句名言:「噢!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當社會高呼自由,而自由也不斷被濫用,談自由更易觸雷,成為被攻擊的對象。
《經濟通》所刊的署名及/或不署名文章,相關內容屬作者個人意見,並不代表《經濟通》立場,《經濟通》所扮演的角色是提供一個自由言論平台。
【你點睇】港鐵失倫敦伊利沙伯線專營權,你認為「國際化」遇挫的港鐵應否將重心轉移回本地?► 立即投票